媒体文章
斑斓暧昧载荣载辱的精神线索(新京报)
发布时间:2008-03-17
将来或者现在家书已成记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和通讯工具的发展,作为曾经最主要交流方式之一的书信日渐式微。而亲人之间的家书,也随着交流逐渐便捷和频繁而几近绝迹。因为如此,曾经承载着亲情的家书凸显出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其不可再生性具有了文物般的意义。几年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等联合发起了“抢救民间家书”的活动,正是出于对家书重要性的认识和考虑。
不同种类的家书
在我国,以家书而成书的有人们熟知的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以及沈从文和家人的《从文家书》,傅雷夫妇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等的《傅雷家书》,新近出版的《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去年推出的《任鸿隽陈衡哲家书》等等。当代思想家顾准,在1974年与其弟陈敏之通信答疑,最终形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辑录的顾准思想。
作为纯粹私人之间的交流,《两地书》、《从文家书》虽然主要涉及爱情。但是,从总体来看,书写人生活的时代气息在时隔多年之后仍扑面而来。根据学者张耀杰在《<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一文的研究,《两地书》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时,已经加入左联的鲁迅,对于原信内容进行了大量的改写和删除。199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的《鲁迅作品全编·两地书》才是原信,张耀杰称,这些原信为重新认定历史事实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据此,他对当年鲁迅参与了许广平等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史实,以及其他相关事件进行了研究,并表示,“《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依然是大同人类中同为精神生命体的寻常男女,拥有人本身所共同的七情六欲甚至于人性缺陷。只是由于《两地书》删改之后的流行传世,使得两个人既惊心动魄又理直气壮的情爱故事在公开化、公共化的同时,又神秘化、神圣化了。”
而《从文家书》中沈从文和张兆和之间的爱情则打动了许多读者。“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炽热的爱情表白,至今仍被今天的读者所向往。这本书几乎收入了张兆和和沈从文一生的通信,其后也成为了学者研究沈从文文学观点的重要资料。从中可以看到,从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一直未能忘情于小说创作,只是囿于现实才不得不作罢。
从《傅雷家书》到《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
而《傅雷家书》和《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虽然都是父子间的交流,但是其内容则大异其趣。《傅雷家书》和《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相同的是,通信的这段时间,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急剧动荡之下。《傅雷家书》中,摘编的是1954年-1966年傅雷夫妇写给儿子的信件。书中所收最后一封信写完不久,傅雷夫妇就自杀而亡。傅雷在信中教儿子如何待人接物、怎样做人,包括怎样理财。时隔多年之后,傅聪曾经表示,这些是自己嫌他烦的,从来没有很好看过,自己喜欢的是爸爸讲艺术讲人生。就在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书信成为人人自危的“罪证”:在1954年底,1955年初,舆论界受命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舒芜把自己手头的成百封的胡风书信统统上交《人民日报》,于是形势直转急下;1957年,当罗隆基受到批判时,浦熙修和萨空了也各自公布了罗隆基的一些私人信件,罗隆基于是百口难辩。因此,叶圣陶和叶至善父子的通信能够留存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尽管,它和叶圣陶先生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较小,其后又受到保护不无关联。《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中的近500封信里,国内国外发生的大事如阿波罗在月球上着陆,柬埔寨政变,国内的如尼克松来访,林彪事件,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打三反”运动等等,在这本父子的通信集里面都有所反映。此外,关于这段时间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叶至善的干校生活等,都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有鉴于此,朱正先生以《家书可征国史》为题,对这些书信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朱正试图在信中找到有关作家萧也牧(原名吴小武)的相关材料的愿望却落了空。此前,根据张羽在《萧也牧之死》中的记录,刚到干校不久,萧也牧和叶至善等人作为弱劳力,分在牛组放牛。直到1970年9月,萧也牧才被调到菜组。10月15日,萧也牧就病逝了。两人曾同在牛组放牛一年多,而叶至善在信件中却没有一次提起。由此可见,家书所承载的内容和意义也是有限的,它在书写之前已经过了写信者的过滤和选择,并且不无遗漏。如果像鲁迅那样大量删改《两地书》,则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导和遮蔽。尽管如此,家书以纸面形式留存了书写者当时对事件的真实想法,比起日后的回忆和追述,会更准确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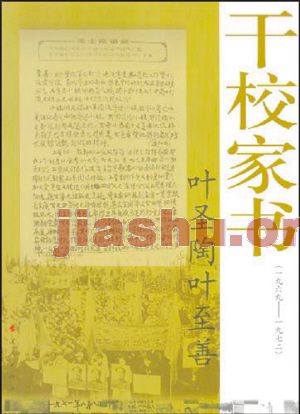



“文革”故事,刚发生就被记录了



“文革”期间,小沫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
叶圣陶与叶至善是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对父子名人,叶圣陶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其子叶至善则是少儿社社长。文革期间叶至善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这对父子给世人留下了将近700万字的家书,最近被整理出版成《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叶至善的侄子叶兆言、女儿叶小沫以及和叶家交情深厚、并审读了全书的学者朱正。
叶兆言
我不能说别人写的干校生活不真实。但是,一个是当时写的,一个是后来的回忆。人在当时的视角和跨越时空之后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叶小沫
后来的回忆录和追述,难免夹杂过来人的感情和看法,已经很不真实了。这个是最真实的,他们当时对毛泽东,对“文革”那样的想法,都是真心的,没有任何虚伪。
【后人访谈】
叶兆言:书信中的干校描写更真实
新京报:两位老人在通信中提到过你,他们通信期间你有多大?
叶兆言:大概十二三岁,这期间,我去过三次北京,有一次因为眼睛受伤,在北京待的时间比较长。
新京报:在书中对于干校生活并没有表现出抵抗情绪,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叶兆言:我觉得,他们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看法是顺应天命:叫你去干校,你不能不去。既然别人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大伯去那里,决不是响应号召,但是也没觉得这是对一个知识分子多么大的摧残,而是很平静地应对。
新京报:他们书信中的干校生活,与我们印象中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叶兆言:书信中写到的干校生活,确实与一般人的印象不太一样。我去过干校,就我看到的情况来说,大家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可能有些人身体不好,容易生病,干校的医疗条件比较差。但是,并不是像很多人后来写到的文章那样,充满了迫害,充满了险恶。这是不真实的。
新京报:但是,很多人在描写自己在干校的时候,说的大多是苦难。
叶兆言:我觉得,在干校的最大痛苦是,知识分子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在经济上,他们都是拿原工资,而他们的工资都是很高的。干校是很闲的,像我伯父他们放牛,真的是淡出鸟来。当然会有家庭分离,夫妻分开。但是,他们这些人都是经过抗战的,经过各种奔波的人。生活上、物质上的艰苦跟过去相比不算什么,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痛苦还是心灵上的,就是不让你干自己想干的事。
我觉得,这些书信里面写到的情况是真实的,我不能说别人写的干校生活不真实。但是,一个是当时写的,一个是后来的回忆。有些后来的回忆确实是有诉说自己公子落难的感觉,人在当时的视角和跨越时空之后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新京报:在书信中,“文革”中的很多事都有反映,但是,两老对“文革”的看法也与一般的“文革”回忆很不一样。与叶老受保护有关吗?
叶兆言:两位老人在书信中对“文革”的看法,并不是因为祖父在“文革”中受保护。现在,很多人把“文革”看成一个整体的概念。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文革”有10年时间,这其中充满了变化。在“文革”初期,冲击确实很强,谁都躲不过。所谓的批斗,主要是前面那一段。有人给我祖父贴了很多大字报,祖父让我堂哥去看,堂哥看完之后简单地描述给他听,祖父也有想不明白的。这个坎在“文革”开始对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平等的,到后来,保护也是同等的。我经常强调的是,“文革”是整个中国人普遍受难。
另外,“文革”印象的形成和个人的描述有关系。而对于事物的看法和人的生活态度有关系。像我祖父的房子,突然住进来两家人。祖父不会非常愤怒或者怎样,而是觉得我这么大的房子,住进来两家很正常。我们家也是这样,别人住到我家来,我家里人觉得这是正常的,没觉得这是迫害。
新京报:叶圣陶和叶至善的父子关系特别亲密,与叶圣陶是一个教育家有关吗?
叶兆言:可能有一点关系。祖父和伯父的那种关系,是我们家庭的一个传统,就是那句老话“多年父子成兄弟”。我和我父亲也是这样,大家很谈得来。
叶小沫 他们对“文革”的看法都是真实的
新京报:你在编《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的时候,经历了怎样的情感体验?有什么顾虑没有?
叶小沫:我编信的时候顾虑很多,怕读者看了,觉得这父子俩对“文革”的看法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看法不一样。但是,这本书不是想说他们是怎么拥护“文革”,而是给“文革”留下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资料,其中包括全世界的大事,市井生活等等。后来的回忆录和追述,难免夹杂过来人的感情和看法,已经很不真实了。这个是最真实的,他们当时对“文革”那样的想法,都是真心的,没有任何虚伪。
新京报:在1972年你的父亲叶至善给你的爷爷叶圣陶的一封信中说,你和弟弟叶永和插队刚开始的时候有一股劲,后来就逐渐消沉了。你父亲认为,这是由于你们以为边疆、农村都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令人欢欣鼓舞,碰到现实后都不如意,以及“缺乏斗争的毅力”所致,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否如此?
叶小沫:我一开始去黑龙江的时候,满怀着要去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但是,看到的现实和我们期望的却不太一样。知识青年中间也搞过阶级斗争,有的知识青年很压抑。我弟弟在陕西插队,本来考上了大学,外国语学校录取他了,外调的时候说我爸爸有问题,结果他没有上成,这对他打击还是挺大的。他当时没有告诉我爸爸这件事,直到和他一起的知青全都走光了,他一个人每天自己下地,自己收工,这样生活了一年多。
我当时所在的黑龙江,倒不像别人说到的云南、内蒙古和陕西插队那么苦,我们始终都能吃到大米、白面、窝头。住的是砖房,工作也不是每天都累得直不起腰来,没到那种程度。而且,当时的机械化程度还很高,比我父亲在信中写到的工作时间也短得多。只是因为身体原因,才不得不回京。父亲说我“逐渐消沉”,可能是我主观上不够坚强,不够坚定。
新京报:那么,你自己如何看待那段生活?
叶小沫:总的来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段生活,我对上山下乡,看到的不完全是它的负面,我们家里人对有些事情的看法,至今也不完全一样。
新京报:你在前言里面说:“如今的我们对那个时候的许多事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却不想对那些事和那些情感全都给予否定。”为什么?
叶小沫:我觉得,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确实是一种锻炼。当时的领导层怎么想的,我不关心,而且,这些事不是我能左右的。“文革”中,像我爷爷那批人,很多都受到冲击,而我爷爷没受到冲击。我们这家人基本上都上山下乡了,没有什么很大的灾难,可能这也算一个特例。这种情况可能影响了我们对那时一些事情的看法,但是,这没有办法。
新京报:家里没有受到冲击,是不是导致你现在对那时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的原因?
叶小沫:我觉得可能是原因之一。如果有家人被斗得很厉害,那么就可能是另一种看法。实际上,我爸爸也受到隔离审查了。他也去打扫卫生,睡地铺。但是,我爸爸也没有觉得特别委屈,因为大家都在被审查。他没怎么提这件事,我们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是不可化解的。这可能跟心态也有关系。
新京报:你回过头来看这些信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有些看法和父亲不一样?
叶小沫:我比较单纯,对于爷爷和父亲的想法,很少抱怀疑态度,老觉得他们说的、做的都是对的,很遵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叛逆的思想。
【专家视点】
朱正改造思想就是这样
新京报:今天看来,《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朱正:我是搞历史的,我自己对这段历史有偏好。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史料。如果谁要研究五七干校史,没有比这更完整的资料。而且写信的两位都是名人。其次,研究70年代,它也是很好的史料。叶圣陶、叶至善父子在信中显示,他们还真是相信了当时的宣传。比如五七干校改造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等等。父子俩真的是把它当作一所学校来看待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迫害。他们当时完全没有这样一种见解。但是,他又把这个过程详细地描写了出来。此外,包括他们的孙子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这些知青自己把上山下乡当作响应党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去锻炼,农村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后来慢慢的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了。
新京报:叶圣陶、叶至善父子为什么会对各种号召深信不疑?
朱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一开始都以为上级的号召都是对的,从字面上去相信它。只不过觉醒有迟有早。如果我没有被打成右派,没有被送去劳动教养,也许我被蒙蔽的时间还要长一点。我刚被打成右派的时候,还真认为自己错了,认真地写检讨,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新京报:按照叶至善在家书中写到的他自己养牛的情况,他的工作并不轻松,但是他并没有觉得苦……
朱正:以苦为乐嘛!脱胎换骨地改造思想就是这样。
新京报:在很多人的回忆中,都说到在“文革”中间不敢保存私人信件,看完之后马上销毁。但是,叶氏父子能够保存这么多完整的信件,为什么?
朱正:叶圣陶在“文革”中是在体制内受到保护的高知高干,在书中也有体现。叶圣陶作为教育部副部长,自己出去旅游,地方行政部门派人招待什么的。以我自己为例,我没有干校生活的经验,当时是被劳动改造,写信首先考虑的是要经过管教干部的检查,所以信里面的内容不完全代表我的真实想法,有时为了讨好管教干部,还要写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但是,叶至善没有这种顾虑,所以写的都是他的真实想法。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张弘
“文革”父子书
书评人 黄集伟
翻开这本书的感觉,与推开邻居家门的感觉多少有点儿像。就算不知道叶圣陶是谁,叶至善是谁,那种热络的气息仍扑面而来。我看见,有个烧得滚烫的煤炉子当屋立着,上面那只铝制水壶吱吱吱冒着热气。水开了,沏上茶,开始唠嗑吧。前面这个并不确切的意象所妄想强调的,无非是那种酱油色的老照片调性,要划痕,要擦伤,要那种类似农耕时代居家生活的凡俗与庸常……是幻觉。可我觉得,这一幻觉撑满了整本书,将那用密密匝匝蝇头小楷写成的厚厚一叠家书里里外外染尽风霜。
当然,换个角度,换个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读者,去想去看,多半会觉得,作为一本读物,《干校家书》并不“好看”。它过于琐碎,过于私人化,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家书,尤其是这种并未计划公开面世的家书,琐碎本就是它最重要的特质,正如我们的蜗居,有了凌乱才有舒坦,有了高高矮矮醋瓶子盐罐子,才有八两饺子一头蒜的滋润。家书不是大文化散文,不是样板间。假使真有一类“家书”整饬高阔气象非凡,我会想,那该是“政府工作报告”吧?
《干校家书》里的第一封家书写于1969年5月2日,最后一封家书写于1972年12月21日,通信时长3年零8个月,而刚好在中国历史上,这3年零8个月的情形相当诡异而特殊。用熟句“烽火连三月”比之拟之,合适。在我读过的数种“文革”回忆录中,像本书这样意外记录一个家庭琐事、情绪状态乃至相互温暖、相互扶持、隐忍、苟延残喘的书,可说绝无仅有。而它的正式出版,也就更在我的预料之外。我承认,这本收入500多封书信、洋洋70万言的家书确为一地鸡毛,可体量庞大的鸡毛,端的不同寻常。它里面没有家国大事,可家国大事是它的底色;它里面没有摧枯拉朽,可摧枯拉朽是它的声效。这是一本蕴含那个年代完整信息的一枚细胞,一枚巨大的细胞。
“牛的鼻子上,到处都用铁环,但这里的农民说铁环伤鼻子,都用木叉或木钩。……”(叶至善致叶圣陶1970-5-18)
这封家书的要义可被概括为“养牛心得”。关于“文革”,“牛棚”二字出镜率最高,可无论抽象的“牛棚”还是具象的“牛棚”,记录叙写得如此周延详尽者,寥寥无几。它里面有意外,有新鲜感,甚至还有编辑家叶至善基于专业惯性的关于“桑”与“伤”我语文考证。而它本身则如一枚铁钩,上面悬挂着一件染满五味的情绪的抹布。当然,在这枚铁钩上悬挂着的,也可能是一顶梦想的草帽或一柄妄想的镰刀,也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它为后人考证一代人的沉浮之运提供了一个丰饶的入口。
“浩然来看我了,十年不见,快谈一个半小时。……他的第二个长篇叫《金光大道》……也是三部,第一部已印成‘征求意见本’,交我一本,我预备认真看。42万字,四五月间要出版。浩然今年四十岁,精神饱满。”(叶圣陶致叶至善1972-2-15)
这封家书里出现的那个四十岁的浩然,那个精神饱满的浩然,那个创作态度、创作企图双高的浩然数周前寂寞离世。我猜恐怕连他自己也早已忘记1972年2月13日晚与叶圣陶的一席谈了。而那一席谈对于后来人而言,则颇堪玩味———在浩然《艳阳天》乃至他呕心沥血、孜孜不倦营造的《金光大道》身后,怎么会没有同行、长者的应酬或唱和?在那个年代,浩然是一个独唱,男高音,可他背后有口无心、有心无口的低声配唱、哼鸣合唱,也不该忽略。否则,那独唱突兀不说,也并不就是真实的舞台表演吧?
“在尼克松来京期间,书店里陈列出《红楼》《水浒》之类的书。买客看见很高兴,抢着买了,到收银柜上去付钱。谁知收银柜上说这些书是不卖的,你就交在这儿吧。大概也引起些口舌。消息也真灵通,外国记者对此事报道了,苏修也广播了,就在以后的一两天内。于是周总理知道了,叫吴德去处理此事,书店就吃了吴德的一顿‘排头’……我以为这些不算大事,但是即小可以见大”……(叶圣陶致叶至善1972-5-6)
隔着三十多年岁月时空隔膜遮蔽,我也觉得,对我们这个伟大文明古国而言,这的确不是大事。可我也同样赞同说,这个小小的粉饰的确可以小见大。它甚至已在巧妙呼应我们的当下、眼前,直至身边……1972年5月6日当然不是如是中国面子文化乃至文化面膜的起始点,可恰恰因此,《干校家书》中随意记下的这一笔,足够珍贵。
说到“文化面膜”,它其实也是我翻本书前最先警惕的关键。叶圣陶:现代著名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编辑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叶至善:著名少儿科普作家、优秀编辑、优秀出版工作者。如果写信人当初知道后人会将这些家书结集出版,会不会有所遮掩和保留?而现在结集出版的这对文化名人家书,会不会一如既往为尊者讳?没想这些疑问在我翻开本书后一一释然。在一个个鲜活真切的细节面前,我的犹豫逐一松动……这是一本没打粉底的家书,面膜之类也被束之高阁……这就是所谓原生态?
我妈要是还活着,今年也奔80了。偶尔想起老人家,印象最深的,是她记了一辈子豆腐流水账。可每次翻阅那些,父辈一代精神底片上的盲点或划痕,仍无法在萝卜白菜炸酱面的确良之类的清单里寻见蛛丝马迹。我的巨大失落在于,我常常会因此惊恐相似的懦弱、卑微、依附、相似的愚忠基因潜在繁衍,绝望遗传。如是阅读预期规定了我在《干校家书》里更在意找寻的,是父辈们斑斓暧昧载荣载辱的那根精神线索。我想说,这条线索我看见了。也正是因为有了它,本书得以超越纯粹个人史、家族史或回忆录属性,成为未来社会学者提取标本见证一段民族耻辱的一部分。我知道,对于一个泱泱大国区区三五年的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而言,它依旧不过碎嘴唠叨,一地鸡毛,如残砖碎瓦,可没有它,在历史墙壁弹洞累累之外,会有更多豁口永远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