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
2008家书更生
发布时间:2008-10-23
【编者按】
在中国文学中,“家书”传统源远流长,既滋养了一个个家庭,又记录了时代。近段时间,民间家书不断被发掘出来,《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为我们填补了历史的细节。而更多“非典型性家书”正被不断创造出来,专栏、博客、小说……都是这些“现代家书”的新载体。2008年的新书,让我们看到了“家书更生”这一可喜的新现象。
【延伸阅读】
《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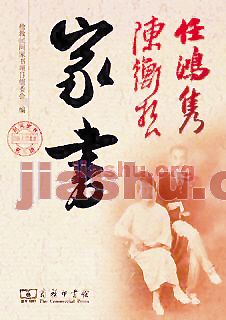
是谁第一个提出科学兴国的理念?又是谁写出第一篇白话小说?任鸿隽、陈衡哲这两个对今天多数人来说感到陌生的名字,曾经承载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第一”。该书是“抢救民间家书”系列第三辑。
《与二哥书》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年6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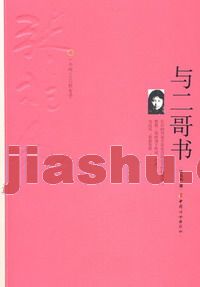
读者感动于二哥(沈从文)三三(张兆和)的爱情,津津乐道他们的鸿雁往来。但仅读《与二哥书》,不会全面了解张兆和,尤其是后期张沈之间的感情,以及解放后沈从文思想的矛盾和痛苦。就此而言,可能造成读者的误读。
《致女儿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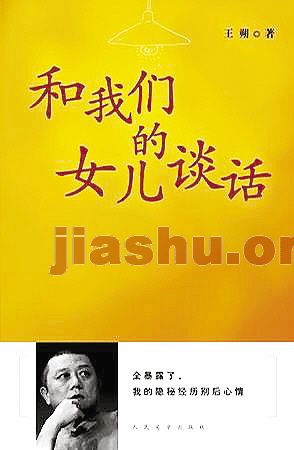
短短半年时间,老王朔连续推出两本和“女儿”有关的书,一封长信,一部小说。这是王朔的第一次“真人秀”,而倾诉的“假想对象”是女儿。对于王朔而言,“对谁说”或许并不重要,“说什么”才是他的关注点。因此,不要期望能从这本书中得到诸如《傅雷家书》那样的谆谆教诲,也不要期待体验像《妞妞》那样催人泪下的款款深情,这只是一个“垮掉派”的忏悔录。
《酱子就可爱》夏瑞红《时报文化》2007年10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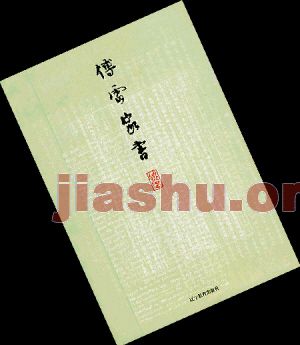
相较于《亲爱的安德烈》里文化、世代与成长等大型矛盾,现任中国时报浮世绘版主编、同时也是人气部落客的夏瑞红,新书《酱子就可爱》则是柔软修行、亲切有味,贴近台湾中产阶级家庭的每日生活。龙应台利用专栏与安德烈“破冰”,夏瑞红则将自己与Bibi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在博客里坦诚托出,最后集结成《酱子就可爱》,也养成一批忠心耿耿的读者,其中还包括Bibi的同学。
以家书而成书的,从影响深远的《颜氏家训》、《朱氏家训》,到后来的《曾国藩家书》、《左宗棠家书》,再到解放前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闻一多家书》,解放后的《傅雷家书》、《从文家书》等,可谓源远流长,由来久矣。这些家书不仅滋润了一个个家庭的成长,也为后人留下一座座“洁白的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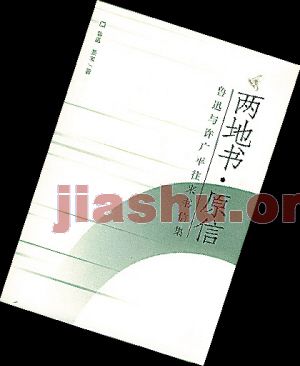 然而,一个事实是,将来或现在,家书都已成为一抹渐行渐远的记忆,其不可再生性使之具备了文物般的价值。于是,民间家书不断被发掘出来,《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让我们重新认识逝去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更多“非典型性家书”正被不断创造出来,专栏、博客、小说……都是这些“现代家书”的新载体。2008年的新书,让我们看到了“家书更生”这一可喜的新现象。
然而,一个事实是,将来或现在,家书都已成为一抹渐行渐远的记忆,其不可再生性使之具备了文物般的价值。于是,民间家书不断被发掘出来,《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让我们重新认识逝去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更多“非典型性家书”正被不断创造出来,专栏、博客、小说……都是这些“现代家书”的新载体。2008年的新书,让我们看到了“家书更生”这一可喜的新现象。
典型性家书《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这是一本没打粉底的家书”

用文字来承载历史,家书和日记都算得上是第一手的材料。新近出版的《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一九六九——一九七二)》,大概是最接近“原生态”意义的家书之典型一种了。
1969年4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叶至善戴着“帽子”前往河南潢川,进入团中央“‘五七’学校”,他的孩子们早已分赴到密云林场、东北兵团、陕北农村。此时,家里只剩下已75岁高龄的父亲叶圣陶先生、夫人夏满子、儿媳和年幼的孙女。此后的3年8个月,是除死亡外父子间最长时间的分离,他们像“打乒乓”般你来我往不间断地通信。近几年,经过叶氏家人的细心整理,将保留的466封信尽可能对应起来,形成了这本70多万字的书信集。
第一封家书写于1969年5月2日,最后一封家书写于1972年12月21日,通信时长3年零8个月。而刚好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段相当特殊的社会现实,用熟句“烽火连三月”比拟,也未尝不可。正因为此,这些足抵万金的家书的正式出版,更在人们预料之外。出版人、书评家黄集伟一早就说了,“文化面膜”是他阅读前最先警惕的关键。叶圣陶,现代著名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编辑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叶至善,著名少儿科普作家、优秀编辑、优秀出版工作者。“如果写信人当初知道后人会将这些家书结集出版,会不会有所遮掩和保留?而现在结集出版的这对文化名人家书,会不会一如既往为尊者讳?”在一个个鲜活真切的细节面前,黄集伟欣然指出,这是一本没打粉底的家书,一部纯粹意义的家书。
阿波罗在月球登陆,柬埔寨政变,尼克松访华,“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洞”,“林彪事件”,四十岁、刚刚写出《金光大道》的浩然……《干校家书》真实记录了叶氏父子在那个特殊时代对“大事要事”的应对和处理,对周围人物悲欢、世态炎凉及其当时的社会动向、思想变化的心态和情感,确是反映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或许,对于一个泱泱大国区区三五年的往事而言,琐碎至极的《干校家书》不过一地鸡毛,可没有它,在历史的废墟之外,将会有更多豁口永远空缺。由此,《干校家书》得以超越纯粹个人史、家族史或回忆录,成为这一段国史的旁证和标本。
非典型性家书《聆听父亲》:个人史延伸出的家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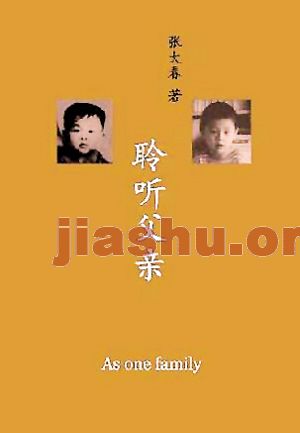
1997年2月6日除夕夜,台湾作家张大春的父亲意外摔倒,从此再没站起。当时父亲是这样向张大春表达感情的:“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从小听父亲讲述家族故事,溯源中国文化历史,很自然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中国文化“乡愁”的张大春,于是在父亲生命进入末期、孩子生命即将开始的这一刻,开始调动生命的全部积蓄,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从哪里来?”这是一部张大春给还未出生的孩子说故事的书,说的正是自己的父亲,以及从父辈那里听来的家族历史。儿子听“我”说,“我”听父亲(以及五大爷、六大爷、二姑等父辈)说,是为《聆听父亲》。
对于内地读者而言,“张大春”这个名字也许陌生,只在2004年广西师大引进过他的《小说稗类》,一本小说理论书籍。但在台湾,他可是当之无愧的一线作家,他的“大头春”系列和《城邦暴力团》等都被读者视为经典。今年1月,世纪文景以《聆听父亲》拉开系统引进张大春作品的序幕。
台湾书商在宣传《聆听父亲》时,声称这是自“白话文学朱自清《背影》以来最感人的父亲书写”。事实上,自从1919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发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一文以来,“父亲”、“家庭”在现代中国的书写中就成了一个沉重的主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以“父亲”和“家史”为主题的书写,也还是较罕见的。近百年来,“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让我们的文学史只有大历史而无小历史,只有国史、族史而无家史、个人史,至于当代甚嚣尘上的现世主义,更让“活在当下”的我辈彻底沦为“无历史的人”了。因此,黄集伟将张大春称为一位“内地所没有的作家”,实在并非过誉。
严格意义上,《聆听父亲》决不是纯粹的“家书”,它更是一部被“创作”出来的小说。全书以与未出生的孩子对话的方式,从祖上五代开始,说到父辈,说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未出生的孩子是虚构的听众,张大春写作的用意只在于——抢救家族记忆。看到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聆听父亲》是写给父亲和孩子的家书,是留给后代的家史,是回忆父亲的散文,更是好看动人的小说。
非典型性家书《亲爱的安德烈》:现代家书不假装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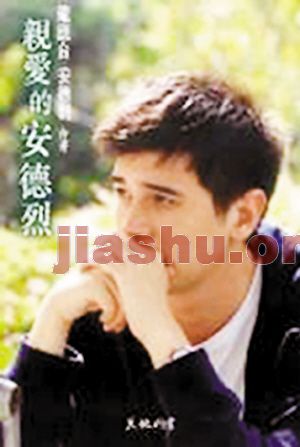
这是一本太有趣的读物。龙应台一直是充满争议的知识分子。年轻时烧出《野火集》,而后“评小说”、“看台湾”,强悍辛辣,所到之处常起风波。然而在新书《亲爱的安德烈》里,她尽褪英锐之气,低下昂然的眼睛。安德烈是龙应台的大儿子,也是老读者记忆中的“安安”。安德烈18岁那年,龙应台发现一切忽然变了,“他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了”。人心之门硬敲是敲不开的,她只好拐弯提议,不如透过文字,两人以书信方式合写一个专栏?出乎意料,中德混血、受全套欧式教育,酷酷的安德烈点头答应,一写3年6个月,最后集结成《亲爱的安德烈》一书。目前,台版、港版均已面世,内地还尚未引进。
“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个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个东西文化。”龙应台和安德烈各自承担起两代的代言人。还好,话题并没有沉重到只有国家、文化、民族、道德,间或有关于衣着品味的调侃,有音乐口味的差异,有对“KITSCH”的笑谈,让这些私人信件非常“好读”。《亲爱的安德烈》是一本跨世代、跨文化的两代交锋对话。借着它的书写,龙应台和21岁的安德烈共同找到一个透着天光的窗口。透过这“天窗”与“天光”,亲爱的青年子女,或许也可以带着这本书去敲敲爸爸妈妈的门。
“这样的家书,是双行道的对话而不是单行道的训话。”评论家马家辉认为,中国其实有着长远的家书传统,政治家的家书,艺术家的家书,教育家的家书,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到傅雷到胡风,上一代给下一代写信,下一代给上一代回信,世代对答,向来不寂寞,但这些对答绝大多数只是训话和听训,我们没能看见真正的沟通。“龙应台与儿子承续了家书传统,却又拓宽了家书风格,在信函的书写史上,开辟了一条小小的新路,这是《亲爱的安德烈》的出版意义。”
今年年初,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周报》主办的2007年度“开卷好书奖”揭晓,《亲爱的安德烈》在“美好生活书”奖项拔得头筹。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仅以港台出版界而言,下一代的教养,突然成了作家们的共同焦虑,“亲子书写”、“现代家书”成为今年非常突出的书写类型。李艳秋写《走一条快乐学习的路》、夏瑞红写《酱子就可爱》,还有,刘墉写给儿子刘轩的那一系列几个月前也交由时报出版重新包装出版。但最有趣的一本,还是写完《聆听父亲》,接着用父亲身份发言让人聆听的张大春《认得几个字》。
时间: 2008-05-05来源:深圳商报 刘悠扬

